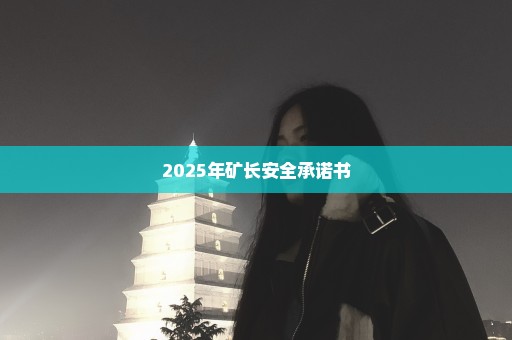庄子和老子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老、庄思想的主要区别在于:老子提供的是比较超然的客观性描述,庄子提供了更多个人主观感受和启示的具体事例。
世以“老庄”并称,庄子和老子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
老子的主要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是什么。老子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二、道的作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而为和。一指混混沌沌的原始,二指由混沌二气生出的阴阳二气,
三是阴阳二气通过冲撞而形成统一;三生万物。三、道的特点。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为无不为,反者道之动。无是虚无的无,无才是最有用的。无为而无不为,反者道之动,是说事物总是向它相反的方向去转化,矛盾依存的双方影响其对立面的转化。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因此通过这两者推出反者道之动;
四、道的规律。事物总是向它相反的方向转化为道的规律,从出生就走向死亡,从成长就走向衰老。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老子说,柔弱胜刚强。比如说一阵大风吹过,大树就要折断,而小草却留了下来。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胜,水是最温柔的,但是用之攻坚又有很大力量。把之中观察事物的方法用于人事,老子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
五、道的本质。老子认为,道的本质是听任万物自然的变化而不加干涉。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之能长久,是听任物之自化,万物之自然。老子把道法自然引人入胜,就得出了无为而治的观点。
庄子的思想,可分为三个主要内容。
一、无为而治。
庄子的无为理由,与老子完全不同。老子的无为,其理由是反者道之动。也就是说,为了实现真正的伟大社会成果,你不要妄动而要遵循规律。老子的无为是为了无不为。而庄子的无为,其理由是万物(也包括所有人)都是自由自在的时候才能接近幸福,管制越多规矩越多就越失去自我,也就越失去幸福。所以任何非自然的规矩,都是压制人的幸福的。
二、逍遥游。论幸福的两种方式。
首先,庄子反对礼和法,以及一切“普遍性”社会道德。因为庄子认为,人与人是不同的,所谓的普遍道德,只不过是削足适履,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已。所以,逍遥游的第一个层次,叫做万类霜天竞自由(瞎引用一下主席的诗词了)。说万物各有其本性,本无所谓高低。只要他们都各自 充分而自由的发挥了自己的自然能力,他们就同等幸福。比如小鸟的幸福就是枝头高歌,大雁的幸福就是千里迁徙。各有各的幸福,但只要都实现了自己的自由,那他们是等同的幸福。
逍遥游的第二个层次,高级的幸福。前面那种是低级的幸福,是有差异的幸福。那种有差异的幸福其实不可能真正圆满,因为万物都不可能真正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万物都受到各种制约。按西哲的说法,想怎么做怎么做是尼采的超人,但后来海德格尔指出,超人不可能实现,因为人世间存在太多的限制,比如:人总是会死的,康熙都还要向天再借五百年嘛,可惜借不到。所以,更高级的幸福,只能是与天地融合。所谓与天地融合,就叫做:天人合一。这个境界,超越了万物的区别,超越了人与世界的区别,我本身也已经感受不到了,人完全融入天地中,于是获得永恒的幸福。
三、齐物论。论知识的三种层次,这代表了庄子的最高境界。知识的第一种层次,是惠施十论的层次——相对论。人人都只掌握片面的知识,妄图用自己对片面知识的定义,来影响别人,获得认可。庄子说,假设我与你辩论。我赢了,就代表我一定对么?你赢了就代表你一定对么?未必。我们再找第三人评判。第三人支持我,就代表我一定对么?第三人支持你就代表你一定对么?未必。一切都是相对的,靠人的讨论人的站队,得不到真理。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这是知识的第一阶段。
知识的第二阶段:照之于天。这个阶段大致等于惠施所谓的大一,小同异上升到大同异。不过惠施仅仅把这个作为最高理想提出来,并没有深入论述。而庄子的最高阶段并非这个阶段,对这个阶段的论述比较详细。万有,也就是各种各样知识,都是来源于“一”的,也就是万物之母的那个唯一的“有”。从道的观点看,每物都恰好是每物的那个样子。万物虽不同,都统一于一个整体,就是一。道行之而成道谓之而然,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无毁复通为一。
知识的第三阶段:混沌与坐忘。既已谓之一,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与惠施不同。庄子认为一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可以思议,则至少言与思就在这个一之外,那就不是真正的一。于是真正的一是不可言说的。于是只能是混沌,达到混沌状态的才能真正掌握绝对的知识。为什么要弃智,因为相对的知识导致区别,而坐忘才能真正同一于天。不过原始的无知,不是有知后的坐忘,二者完全不同。
他们的不同:
庄子认为生死齐一,无就是有,有就是无,实则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其意常超出生死有无之上。及其末流,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故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因而有与世同波、安时处顺一说,老子认为天道无为,实则无为无不为并重。《道德经》上下两篇,一曰道,一曰德,德者得也,两篇中一半篇幅是在讨论“得”。“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用心乃在不去。庄子在社会观方面,只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所谓“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恢恢乎其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其精义为艺术论。老子在社会观方面是一种独特的治世哲学,所谓“反者道之动”,“负阴而抱阳,知雄而守雌”,“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章、二十八章、四十三章。),其精义合于兵法。《庄子·知北游》:“光耀曰:‘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以至此哉!’”对于绝对知识的追求如同飞蛾扑火,有一去不复返之势,在抽象思辨的本体论方面长足进取,一贯到底。而老子在本质上则是致用的。老子说:“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行文常以圣人称,如侯王之说策。致用治世和消极处世,这是老子和庄子的最大差别,也是老子所以能先于儒墨诸家而与秦及汉初的政治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早期道家学说在社会政治实践上共有三条出路。其一是老子的“无为而治”。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战国汉初又称为“君人南面之术”、“黄老道德之术”。汉初,儒学也称为“儒术”,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与儒学同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其二是庄子的齐生死和归根,认为人生的意义是被动的,生如得死如丧,因此要安时处顺。这基本上是指人的生命价值而言,是一种人生观,而不涉及社会政治因素。其三是庄子的随波逐流,要求人要因俗、因众,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一种消极处世的社会观。此外,在秦汉以后又有道教和方士,在人生和社会实践上主张养生、长生,有符录、内外丹等方法流派,但都已不是早期道家的本意。
道家在逻辑思维形式上有“相反相成”和“大象无形”两种高低不同的层次。相反相成是两个相反相成的概念互相对立,比如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等。大象无形是绝对的独立自存的概念,具有最大范围的内涵和外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相对称的概念与之对应,没有任何概念与之相参照,以致于这个概念本身也无名无形。这个概念比如称作“大方”、“大器”、“大音”、“大象”、“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辩”等等。老子再三论述的"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中的“翕”与“张”,“弱”与“强”,“废”与“兴”,“夺”与“与”,和“曲则全,枉则正”中的“曲”与“全”,“枉”与“正”,“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的“柔”与“坚”等等,都是属于相反相成的层次中的成对的概念。老子在哲学本体论上虽然有道论的形而上学的成就,但是在政治观和社会观上,却很大程度地引申于较低的相反相成的层次。而 庄子主张“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所可用乃为予大用”,庄子的人生追求是要求与“大象无形”的绝对概念相一致。老子多言阴阳,庄子多言有无。阴阳是相互对应的一对概念,二者互为消长。有和无不仅是相互对应,而且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二者异名同实,各自代表着抽象思辨中的不同环节。阴阳是宇宙构成的概念,有无是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老子注重阴阳对立概念的倚伏变化,其结果自然是要倾向为一种人道实践的策略方术。而庄子执着于本体论上的一贯追求,其结果也只有以牺性人的独立人格和人生实践为代价。《庄子·天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人之于道,如同器物之于大冶造化,须怀着十分的恭敬,谨慎郑重,决不可以任意。
老子和庄子虽然有极为相同的道论、认识论和逻辑推理,虽然同为早期道家的哲学大师,但是在社会实践方面,却有着不同层次的引申,有着方向相反的哲学目的和社会观。老、庄虽同为道家大师巨匠,但如从人道和政治实践的角度予以划分衡量,二人却要属于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想体系。老子与早期儒家以及其他先秦诸子趋向一致,而庄子则独立于诸子百家之外。以上是对于老子和庄子的浅析。
圣人和亚圣有什么区别
一、康有为区分的九种人
在《礼运》篇中,孔子言大同之世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篇》言大同只是这么寥寥数语,言小康则长篇巨幅,但康有为只将孔子的这几句话抽离出来加以发挥,作《大同书》,写成煌煌数十万言。
据康有为《大同书题辞》所言:“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年),清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生民,著《大同书》。”[1]康子喜欢倒填年月,因此关于《大同书》作于何时一直争论纷纭。但《大同书》并非一蹴而就,康有为写作《大同书》应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2]康有为作《大同书》之时,清政府内忧外患,摇摇欲坠。外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节节败退,割地赔款,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内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并交织在一起,各地大小规模的起义不断。康有为欲挽颓势,欲究富强之道,近希望解决清代内忧外患之境,远欲使中华民族可以再度执世界之牛耳。康有为从《礼运篇》获得灵感,以立法师自居,欲为中华民族制定新时代的“宪法”,欲将中国建成大同社会,于是作《大同书》。《大同书》是康有为的救世之书,是其建国方略,也是他“为万世开太平”之书。康有为说:“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致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治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3]从康子自述之中,其志向可见一斑。康有为弟子钱安定为《大同书》所作之序,颇得康有为用心,他说:“《大同书》者,先师康南海先生本不忍之心,究天人之际,原《春秋》之说,演《礼运》‘天下为公’之义,为众生除苦恼,为万世开太平致极乐之作也。”[4]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想象了大同之世的景象,那里没有级界、种界、行界、家界、国界、产界等诸苦,人也不分等级。尽管大同之世人无差等,人人平等,但于智、仁尚有差别。基于此,康有为对未来之世的人群作了总体划分,分为九类。康有为言:“凡仁、智兼领而有一上仁或多智者,则统称为美人。上仁、多智并领者,则统称为贤人。上仁、多智并领而或兼大仁或兼大智,则为上贤人。大智、大仁并领则统称为大贤人。大智、大仁并领而兼上智者,则可推为哲人。大智、大仁并领而兼至仁者,则可推为大人。上智、至仁并领而智多者,则可推为圣人。仁多者,则可推为天人。天人、圣人并推,则可合称为神人。”[5]九种人涵盖殆尽大同世之人,自下而上分别为:美人、贤人、上贤人、大贤人、哲人、大人、圣人、天人、神人。此九种人的概念采自儒家和道家,譬如贤人、大人、圣人出自儒家;神人、天人云云出自庄子。九类人起点为美人,终点为神人。康有为将贤人三分:贤人、上贤人、大贤人。贤人之所以三分,可见其人数之多与重要,贤人或可谓大同之世的中坚力量。透过康有为所划分的九种人,我们一方面能看到康有为《大同书》的用意,一方面也能看出其问题。 二、庄子区分的七种人 康有为区分了九种人,其灵感来自庄子《天下篇》。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曾多次引用庄子《天下》篇,可见康有为对此篇之重视。《大同书》所区分的九种人,其名亦与庄子在《天下》中的命名相合,譬如圣人、天人合神人直接就是出自《天下篇》。康有为划分的九种人应是庄子在《天下篇》中所划分的七种人之变,变化了什么和怎么变化恰能见出康子的怀抱。《天下篇》在庄书中地位极重要,可谓全书后序[6]。《天下篇》讲述了先秦学问源流,也是庄子对各家学问优劣的总体判断。在《天下篇》中,庄子区分了七种人,自上而下谓之: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民。庄子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庄子看透了世界,他所区分的七种人可将所有的人纳入其中,且每种人的品质与特征涵括殆尽,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人群皆可以分为这七种人。庄子的七种人应是孔子所谓上智下愚的细分,亦是《诗经·大雅·抑》所谓哲与愚的细分。上智与下愚、哲与愚是人群的顶端与末端,然人群二分只是言其大概,中间的系列不甚明了,庄子七分则能将所有人定位,并将所有人的性质概括殆尽。七种人次序的排列以及圣人在这个系统中处于什么位置,以我目力所及,有两种意见比较精彩。一以谭戒甫为代表,根据他的分析圣人在这个系统中虽处于第四位,但却是这个系统的中心,他说:“圣人以上,有至人、神人、天人,共四层,为神之属,即内圣之事;圣人以下,有君子、百官与民,共四层,为明之属,即外王之事;总凡七层:其所以下降上出者,皆由圣人为之中枢而生之成之也。盖圣人实兼内圣外王而一之:其神圣之三与明王之三,皆由于圣人之一,故曰有所生、有所成也。” [7]一以张文江先生为代表,张文江言圣人处于第四位,圣人是至人、神人、天人的翻译,他可以懂得上面三种人,可以将上面三种人的话翻译给后面三种人,但君子、百官和民却不懂得上面三种人,他们需要圣人的翻译;但这个系统可以循环,至人、神人、天人则可以隐藏在民、百官、君子或圣人之中。[8]《天下篇》中民与百官的位置很少存在争议,盖因他们的位置清清楚楚,唯有争议者在于如何理解圣人、至人、神人、天人之间的关系。天人、神人、至人、圣人或不世出,但民与百官绝对是社会的大多数。若民与百官中的君子多一些,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正常运转,各方面皆能平稳;若百官与民中的君子很少,那么这个社会可能就会风气败坏,也难行之久远。 三、二者差别 康有为言九种人是自下而上言之,庄子言七种人是自上往下言之。庄子自上往下言之,说明庄子处于人群最顶端,他可以纵览全局,故能理解全部七种人。但至于庄子处于天人、神人、至人哪一个位置,非我所能判断,但庄子最少应是上面三种人。康有为自下往上言之,但康子未必懂得全局。康有为很小就自比圣人,故被目为“圣人为”。康有为曾自述其二十一岁时之经历言:“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9]康有为“及赴礼部试,题为‘达项党人曰大哉孔子’,而有为试文,结语曰:‘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盖隐以自况也。”[10]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遭到慈禧的追捕,脱险后作《我史》,此书可以化用孔子的一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为“天生德于予,其慈禧如予何?”其自信与抱负,可见一斑。尽管康有为自比圣人,但在庄子七种人这个谱系之中,康有为或只在君子左右的位置,在其设想的九种人谱系中,康有为或在大贤人左右的位置。[11]康有为尽管设想了九种人,但他未必能够把握全局,其对上面几种人的定位或多想象。康有为对九种人的区分,若以庄子七种人而论,只是自君子至天人的再细分,康有为将庄子的前五种人变为九种人。康有为九种人之最低者谓“美人”,其特点为“仁、智兼领而有一上仁或多智者”。康有为的“美人”相当于庄子的“君子”,君子是大同社会中人的起点。但庄子七种人之最下两者,百官和民,在康有为的大同系统中缺失。百官崇刑名尚法律,只是事务性存在;民只关心衣食住行,是自然欲望性存在。庄子的后两种人是人群的绝对多数,君子亦或多有之,但圣人、至人、神人和天人则不世出或是少数中的少数。
康有为建构的大同世界,占多数的民完全消失,竟然全是君子以上之人,大同社会可谓一个君子国。因为大同社会中,全是君子以上之人,人人皆能自理、自治,故百官亦不必存在。庄子言百官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百官是事务性存在,与法、名等有关。《联邦党人文集》所谓,若人人是天使,那么就不需要政府了,《易》所谓“群龙无首”,若社会中人皆是天使或龙,那么百官确实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民在大同社会中也不再存在,盖因民可以脱离事、衣食、蕃息畜藏而进至九种人之中,可以成为美人、贤人、上贤人、大贤人、哲人、大人、圣人、天人、神人。因此在大同社会中,民也没有了。
庄子立论基于现实,现实中的人群确实有少数人和多数人之分,永远是龙蛇混杂,凡圣同居。对少数人的要求不能强加给多数人,若一旦将对少数人的要求强加给多数人,就会对多数形成伤害,社会风气也会败坏。若要施政,一定要认清现实,分清人群。譬如王安石,他在变法之际,谈及俸禄之制,亦曾大略将士人区分为三种:小人、中人和君子。王安石曰:“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以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12]如此立论或施政,方能切中现实。康有为九种人的立论则是基于理想,他假想未来之世人人皆是君子或比君子层次更高之人。庄子基于现实,他看懂了当时的时代,其实也看懂了所有的时代,每个时代中的人皆如此。庄子立论也是基于对城邦的理解,城邦永远都是建立在意见之上,不可能建立于真理之上。其实西方的很多哲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都根据现实将社会中的人作了区分。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把人分为三种,一种是追求利益的人,一种是追求荣誉的人,一种是追求真理的人。三种人的基本取向不同,对其要求自然应该不同。再如尼采,在谈到人类生活与宗教的关系时,他区分了三种灵魂类型:一是热爱智慧的人的灵魂类型、二是王者的灵魂类型、三是普通人或大多数人的灵魂类型。[13]尼采区分的三种灵魂类型其实就是上智与下愚之外加了一个王。这三种灵魂类型对于宗教的诉求和理解不同,因此不能混同。
康有为作《大同书》是对《礼运篇》的抽象。《礼运》篇,孔子的对话者是子游,其为孔门杰出人物。《论语》言“文学,子游、子夏。”《礼运》篇是孔子口说给子游,是说给了“有耳能听者”,而非说给所有人。康有为忽略了孔子原意,忽略了孔子讲此篇的具体情境,即时刻、环境以及听讲者。《礼运》言:“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此段交代了《礼运》篇发生的时刻,即在“蜡宾”之后。地点则在“观上”。言偃在侧,孔子有所感,心动而“喟然而叹”,如此引起言偃发问,故有孔子之言。康有为将《大同书》笔之于书,虽言“秘不示人”,但曾口说给万木草堂众弟子,以至于万木草堂的诸位弟子多言大同,又经梁启超、陈千秋等人“锐意宣传”,“大同”观念于是大为流行。笔之于书之《大同书》可以传达给不同的读者,康有为非但不睬“微言大义”的写作方式,反而颇多鼓动之辞。康有为之所以不“隐微写作”,盖因其不相信人群分为有智慧的人和粗鄙的人,康有为相信可以启蒙粗鄙者,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有智慧的人。城邦之所以建立,之所以可以牢不可破,是因为城邦成员可以接受共同的意见。康有为则认为城邦可以建立在真理之上,这样的城邦可以称之为大同社会。孔子言:“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又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康有为“移”了人群中的“下愚”,在他的想象中,此后人群中不再有下愚,皆可以成为上智。
康有为设想了一个大同景象,提出一种方案,并且希望将这种方案付诸实践,以之改造世界,改造城邦,改造人民。若人人皆是天使,人人皆是龙,这样的社会自然无敌于天下了。康有为曾讥讽朱熹对于“格物”的解释,言:“而以之教学者,是犹腾云之龙强跛鳖以登天,万里之雕诲鴬鸠以扶摇,其不眩惑陨裂,丧身失命,未之有也。故朱子格物之说非也。”[14]我们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评康有为如下:而以大同教众生,是犹腾云之龙强跛鳖以登天,万里之雕诲鴬鸠以扶摇,其不眩惑陨裂,丧身失命,未之有也。《大同书》陈义甚高,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之志向;然而此书危害亦大,因为康有为不顾少数人和多数人之分别,将高义陈于众人,最终伤害了中华民族。
定义不同、代表人物不同等。
定义不同:圣人指的是在道德、思想、艺术等方面达到极高境界的人,被广泛尊崇和敬仰。亚圣是指仅次于圣人的人,在某些方面具有卓越的成就和贡献。

代表人物不同:被尊为圣人的人物包括孔子、老子、庄子等,在不同的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亚圣通常指的是在某一特定领域或时代中仅次于这些圣人的重要人物,例如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树宸”,尊称为“亚圣”。
鹏仔微信 15129739599 鹏仔QQ344225443 鹏仔前端 pjxi.com 共享博客 sharedbk.com
图片声明:本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本站只作为美观性配图使用,无任何非法侵犯第三方意图,一切解释权归图片著作权方,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有恶意碰瓷者,必当奉陪到底严惩不贷!
 百科狗
百科狗